*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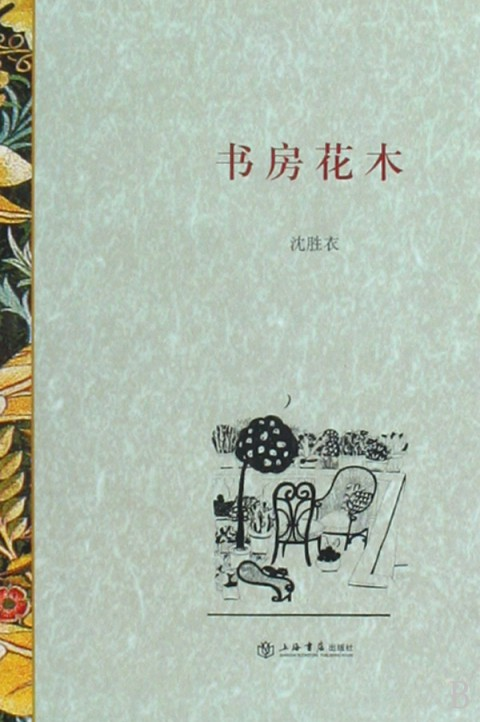
沈胜衣,东莞人,出版有《书房花木》、《笔记》、《闲话》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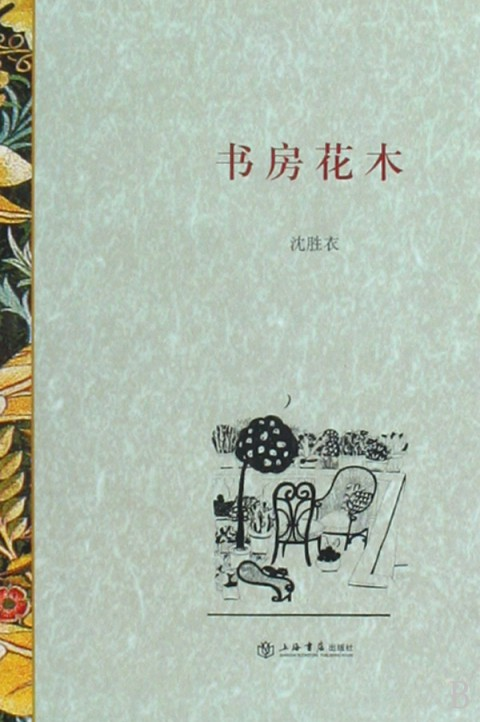
沈胜衣,东莞人,出版有《书房花木》、《笔记》、《闲话》等
进入二〇一六年,颇买了一些书名含有“六”字之书,作为流年时光的书趣,选六种记之。
首先是几个恰好对应的年份:伊迪丝·霍尔登的《一九〇六:英伦乡野手记》(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三月一版),是一个英国乡村女教师的自然观察图文日志;索朗日·布朗的《中国记忆,1966》(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一月一版),是一位法国女外交官在几个城市的摄影作品,可让人直观认识一百一十年前的英国草木虫鸟、五十年前的中国风云片段。这两本在此都只存目,重点看看六百五十年后的世界,看那里草木与风云之间的微妙关系。
说的是《2666》(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一月一版),智利早逝天才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代表作。这部广受热捧的经典,被称为“长篇小说的长篇小说”、“世界文学的《清明上河图》”,书中写了现当代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各式各样人物,揭示人性恶的膨胀,无法遏制和逆转的疯狂;书名2666,乃作者预言人类自我毁灭的丧葬之时。——对于那种此前此后、域中域外一以贯之的“人类丑恶和凶残的本质”,译者赵德明在《译后记》和附录文字中颇有愤慨之笔,并指出,“书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但作者“口气是冷漠和镇定的”,认为作者出于“哀莫大于心死”的绝望,让书中一些角色放弃理想逃避现实。
可是,我感到这部巨著的结尾情节很有意思,似乎是对译者批评的预设回应。全书的中心人物阿琴波尔迪在吃“三味冰激凌”时遇到一位老人,后者向其介绍自己的祖先、一个爱好植物和园艺的学者,他每次旅行的最终目的都定位在被遗弃的花园,从杂草和荒芜中发现花园的美妙之处;同时,“他那些小册子,虽然披着植物学的外衣,却充满了睿智的见解。你通过看那些小册子,可以对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形成相当接近实际的看法”,他并非对现实的暴风雨和人性的多变漠不关心,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提出抗议。“他感兴趣的是人类尊严,是植物。”但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和阅读他了,他的史册留名,仅仅是因为用植物学知识发明的三味冰激凌流传下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寓言,作者以此来结束全书,提供了一种对人生、对世事的取态,就像米兰·昆德拉《笑忘录》里说的:自家园子里的梨子,比入侵的坦克更重要、更永恒。你可以说这是冷漠的逃避现实,但他们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应对荒谬(将时代的暴风雨和个人看法寄寓在花草中,同时又能在败落的花园寻得生活的美好);你可以说那植物学家最后被遗忘的结局,说明他的选择“然并卵”,但他起码做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给世间留下带有草木芬芳的冰激凌,哪怕这里面有苦涩的错位,却能让人品尝美味。
世事如此,也许就只能如此吧,一方面不肯放弃高贵的理想,一方面“放心知其无解”,只专注于内心的尊严,就像德国鲁多夫·洛克尔笔下的《六人》(巴金试译,三联书店二〇一五年九月一版)。
此书副题为“六条人生路”,通过六位世界文学名著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等等,来探讨人生与世界。恰好,今年是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他们的共同忌辰被定为世界图书日(四月二十三日),在此期间读该书中《哈姆雷特的路》、《董·吉诃德的路》两章,聊作个人的小小致意。
按照本书作者的归纳,哈姆雷特是思虑派,沉浸于思考而弱于行动(很多对人生的永恒之问,早已出于这位丹麦王子);堂吉诃德则是行动派,热切追求梦想却没有用现实的理性去思量(翻译《堂吉诃德》的杨绛也在今年仙逝了)。这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当然发人深思,然而,让我印象更深的却是一篇书评的再度归纳:赵越胜的《永恒的困惑》。
其实,我这回选读只是对少年心路之书的重读,因为这《六人》本属大学时接触的作品,当初正是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号《读书》上读了赵越胜那篇书评,震撼不已,启悟不浅,后在学校图书馆借阅;现于学子时光远逝之后,“重聚惟有书”——重新买回大学时借读过的好书——所购是三联经典丛书“文化生活译丛”之“纪念版”,那也真是个人的心情纪念了。
再次翻出那期旧《读书》的赵文,当年读时密密麻麻划满了线,让我激动沉思、至今还能记起的,如:“高贵的唐·吉诃德,我向你致敬。自你走后,这世界变得多猥琐……”下面是好几段对这个抛弃理想、埋头现实的世界的精彩概括、愤然指控,令人发聋振聩;而作者把不问成败、只听从内心召唤的唐·吉诃德树为英雄,“因为绝对律令不问理想能否实现,而只问理想是否存在。”又如文章最后指出,即使本书通过六人而对“人是什么”寻到了谜底,但读来仍觉困惑,那么,“不如放心知其无解……”像这样似乎相悖而又并存的两种态度,对青春期的我影响至深,属于八十年代的心灵激荡。
这些自然是旧话了,连《读书》本身的精神和风貌,都早已随时间转换得面目全非。重温故纸堆,面对自己那些昔年划痕,以及心痕,默默旧怀如涌。但虽则时年飞逝,其心至今未泯。
消逝的八十年代,我一直将其与魏晋六朝联系起来,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文盛世美好时代。后者还要更辉煌、更令人倾慕,“畸美属于魏晋”,“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是早就倾心收集的专题,为二〇一六年选“六之书”,自然少不了再添一种六朝人物,遂买了日本吉川忠夫著《六朝精神史研究》(王启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一月一版)。
此书着重研究“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其中有一部分专门写“沈郎”的原型沈约,且是作者“附加了自我感情”去写的,最为相宜——我因为所取的笔名,向来对沈约特别关注。
沈约的人生路和精神史,确是值得研究的传统知识分子个案,不过这里不展开谈了。倒是更广为人知的唐寅,有着路径相反而同样况味复杂的人生选择——他们都像那“六人”。在二○一六年元旦,查检“六”字开头的词语以作开年凑趣,当中有佛家的六如之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人世正“应作如是观”啊,于是想起六如居士唐寅,乃购《六如居士集》(应守岩点校,西泠印社出版社二○一二年四月一版)。但买后才想起,自己早就有一本大同小异的《唐伯虎全集》。近年已几次因时间相隔太久忘记了而重复买书,人到中年,记忆衰退,可叹焉。
唐寅自然不仅是民间传奇里那个风流潇洒的唐伯虎,当年买《唐伯虎全集》,就因有感于其天才、敏感、绝望、行乐、不计功业文章、追求生活自由。本书点校者《前言》中也将其人格概括为:清醒的生命意识,狂傲的反叛精神,世俗的生活追求。为了这种好感,前几年在苏州,曾专门到桃花坞寻访其遗迹。很美的地名,但实质是一片破落的旧民居,在冷落小巷中转了老半天几乎累坏,才终于看到了唐寅故居、唐寅祠,却都已残败不堪、等待拆迁了,正如自己早年在《唐伯虎全集》书扉写下的:“才子风流不复矣”。
——草木,风云,时代,记忆,景物,才子,皆如露如电焉。
首先是几个恰好对应的年份:伊迪丝·霍尔登的《一九〇六:英伦乡野手记》(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三月一版),是一个英国乡村女教师的自然观察图文日志;索朗日·布朗的《中国记忆,1966》(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一月一版),是一位法国女外交官在几个城市的摄影作品,可让人直观认识一百一十年前的英国草木虫鸟、五十年前的中国风云片段。这两本在此都只存目,重点看看六百五十年后的世界,看那里草木与风云之间的微妙关系。
说的是《2666》(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一月一版),智利早逝天才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代表作。这部广受热捧的经典,被称为“长篇小说的长篇小说”、“世界文学的《清明上河图》”,书中写了现当代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各式各样人物,揭示人性恶的膨胀,无法遏制和逆转的疯狂;书名2666,乃作者预言人类自我毁灭的丧葬之时。——对于那种此前此后、域中域外一以贯之的“人类丑恶和凶残的本质”,译者赵德明在《译后记》和附录文字中颇有愤慨之笔,并指出,“书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但作者“口气是冷漠和镇定的”,认为作者出于“哀莫大于心死”的绝望,让书中一些角色放弃理想逃避现实。
可是,我感到这部巨著的结尾情节很有意思,似乎是对译者批评的预设回应。全书的中心人物阿琴波尔迪在吃“三味冰激凌”时遇到一位老人,后者向其介绍自己的祖先、一个爱好植物和园艺的学者,他每次旅行的最终目的都定位在被遗弃的花园,从杂草和荒芜中发现花园的美妙之处;同时,“他那些小册子,虽然披着植物学的外衣,却充满了睿智的见解。你通过看那些小册子,可以对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形成相当接近实际的看法”,他并非对现实的暴风雨和人性的多变漠不关心,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提出抗议。“他感兴趣的是人类尊严,是植物。”但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和阅读他了,他的史册留名,仅仅是因为用植物学知识发明的三味冰激凌流传下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寓言,作者以此来结束全书,提供了一种对人生、对世事的取态,就像米兰·昆德拉《笑忘录》里说的:自家园子里的梨子,比入侵的坦克更重要、更永恒。你可以说这是冷漠的逃避现实,但他们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应对荒谬(将时代的暴风雨和个人看法寄寓在花草中,同时又能在败落的花园寻得生活的美好);你可以说那植物学家最后被遗忘的结局,说明他的选择“然并卵”,但他起码做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给世间留下带有草木芬芳的冰激凌,哪怕这里面有苦涩的错位,却能让人品尝美味。
世事如此,也许就只能如此吧,一方面不肯放弃高贵的理想,一方面“放心知其无解”,只专注于内心的尊严,就像德国鲁多夫·洛克尔笔下的《六人》(巴金试译,三联书店二〇一五年九月一版)。
此书副题为“六条人生路”,通过六位世界文学名著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等等,来探讨人生与世界。恰好,今年是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他们的共同忌辰被定为世界图书日(四月二十三日),在此期间读该书中《哈姆雷特的路》、《董·吉诃德的路》两章,聊作个人的小小致意。
按照本书作者的归纳,哈姆雷特是思虑派,沉浸于思考而弱于行动(很多对人生的永恒之问,早已出于这位丹麦王子);堂吉诃德则是行动派,热切追求梦想却没有用现实的理性去思量(翻译《堂吉诃德》的杨绛也在今年仙逝了)。这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当然发人深思,然而,让我印象更深的却是一篇书评的再度归纳:赵越胜的《永恒的困惑》。
其实,我这回选读只是对少年心路之书的重读,因为这《六人》本属大学时接触的作品,当初正是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号《读书》上读了赵越胜那篇书评,震撼不已,启悟不浅,后在学校图书馆借阅;现于学子时光远逝之后,“重聚惟有书”——重新买回大学时借读过的好书——所购是三联经典丛书“文化生活译丛”之“纪念版”,那也真是个人的心情纪念了。
再次翻出那期旧《读书》的赵文,当年读时密密麻麻划满了线,让我激动沉思、至今还能记起的,如:“高贵的唐·吉诃德,我向你致敬。自你走后,这世界变得多猥琐……”下面是好几段对这个抛弃理想、埋头现实的世界的精彩概括、愤然指控,令人发聋振聩;而作者把不问成败、只听从内心召唤的唐·吉诃德树为英雄,“因为绝对律令不问理想能否实现,而只问理想是否存在。”又如文章最后指出,即使本书通过六人而对“人是什么”寻到了谜底,但读来仍觉困惑,那么,“不如放心知其无解……”像这样似乎相悖而又并存的两种态度,对青春期的我影响至深,属于八十年代的心灵激荡。
这些自然是旧话了,连《读书》本身的精神和风貌,都早已随时间转换得面目全非。重温故纸堆,面对自己那些昔年划痕,以及心痕,默默旧怀如涌。但虽则时年飞逝,其心至今未泯。
消逝的八十年代,我一直将其与魏晋六朝联系起来,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文盛世美好时代。后者还要更辉煌、更令人倾慕,“畸美属于魏晋”,“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是早就倾心收集的专题,为二〇一六年选“六之书”,自然少不了再添一种六朝人物,遂买了日本吉川忠夫著《六朝精神史研究》(王启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一月一版)。
此书着重研究“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其中有一部分专门写“沈郎”的原型沈约,且是作者“附加了自我感情”去写的,最为相宜——我因为所取的笔名,向来对沈约特别关注。
沈约的人生路和精神史,确是值得研究的传统知识分子个案,不过这里不展开谈了。倒是更广为人知的唐寅,有着路径相反而同样况味复杂的人生选择——他们都像那“六人”。在二○一六年元旦,查检“六”字开头的词语以作开年凑趣,当中有佛家的六如之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人世正“应作如是观”啊,于是想起六如居士唐寅,乃购《六如居士集》(应守岩点校,西泠印社出版社二○一二年四月一版)。但买后才想起,自己早就有一本大同小异的《唐伯虎全集》。近年已几次因时间相隔太久忘记了而重复买书,人到中年,记忆衰退,可叹焉。
唐寅自然不仅是民间传奇里那个风流潇洒的唐伯虎,当年买《唐伯虎全集》,就因有感于其天才、敏感、绝望、行乐、不计功业文章、追求生活自由。本书点校者《前言》中也将其人格概括为:清醒的生命意识,狂傲的反叛精神,世俗的生活追求。为了这种好感,前几年在苏州,曾专门到桃花坞寻访其遗迹。很美的地名,但实质是一片破落的旧民居,在冷落小巷中转了老半天几乎累坏,才终于看到了唐寅故居、唐寅祠,却都已残败不堪、等待拆迁了,正如自己早年在《唐伯虎全集》书扉写下的:“才子风流不复矣”。
——草木,风云,时代,记忆,景物,才子,皆如露如电焉。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日,腊月初一整理毕;
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修改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