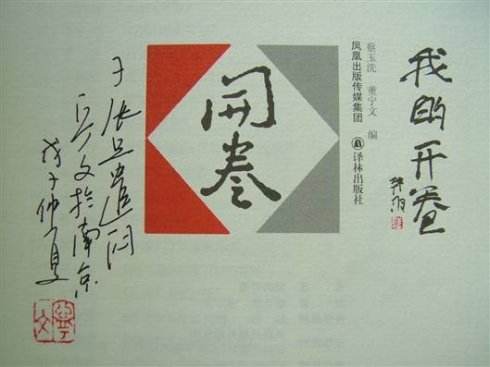
宁文笔迹
对此,南开大学教授李剑国早有妙解:“振良的‘饱蠹斋’或许是自谦的意思,但我更倾向于后一种意思,就是以蠹鱼自许,甘做个书虫子,大饱肚肠。
他的饱蠹斋中肯定还有不少好东西,希望他再选择一个什么题目,继续做下去,不唯自己啃出味道,于读者如我辈,庶几亦可饱其蠹腹矣。”
这个再选择题目,也应当包括他对《开卷》的专题研究,还有两大篇已经问世,一篇是《从〈开卷〉现象说到民刊出路》,还有一篇是为《开卷闲话十编》所写的序言。
然而,如说此中资历,他并不是《开卷》的第一批受赠者,也没有发表过文章。这在《开卷闲话十编》的王序中,有他的夫子自道:“二〇〇三年即接触《开卷》,结缘时间不能算短。虽多是断断续续地读,但这小册子给我的印象,却总是挥之不去,乃至直接影响到我后来创办《天津记忆》等。”
正是有了这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有了他后来为之补全的搜寻。关于《开卷》创刊号的搜寻,叶梓在《我所知道的〈开卷〉及其创刊号》中说:他对一些民间刊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开卷》的创刊号,因相见恨晚而失之交臂。当我把此遗憾通过网信给董宁文说出后,二〇〇七年的深冬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我意外地收到《开卷》创刊号(《我的开卷》第十五页)。”
叶梓是甘肃一家报社的编辑,身居边陲之地,尚知《开卷》大名,尤此可见它的创刊号是多么抢手。王振良的补全办法,除了向董宁文求助,另外就是进行网购。他网购的次数之多,从《记忆的碎片》中的一则小书账,即可知其一二:
“南京艺轩书店郑飞玲寄来《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22元。北京涵泳斋李其功《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1910—1998)》,10元。长春玲儿书屋张春萍寄来《清未小说丛考》(樽本照雄著,日本版),163元,芜湖春田的书摊寄来《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一一北京大学中文系55班纪事》,54元。江西万载县Book的书摊(袁宇)寄来《桂林文史资料》(第三辑),16元。”
这则小书账,出自《八里台的当年风雅》附录纪事篇,由此小书账可知他的网购之频,补全《开卷》自然不在话下。《记忆的碎片》为《天津记忆》丛书之一,《天津记忆》创办于二○○八年,关于创办初衷,张元卿在序言《综汇群芳开盛业》中说:“世人谈论天津,恒以‘文化沙漠’视之,有人对此颇感不平,这就是我的朋友王振良。”不平就要改变其现状,于是,“与友人自掏腰包印行,终于使这个俗称‘小白本’的所谓民刊,成了天津文史研究者必读的抢手货,至今已出版一百余期,默默地改变了天津的学术生态。”
所谓“小白本”,乃是指它素面朝天的封面而言,换句话说,就是开本装帧均师承于《开卷》。知此,即知他为何说《开卷》所留下的印象总是挥之不去了。有此师承,将《开卷》纳入问津书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有了挥之不去的印象,在庆贺《开卷》创刊十五周年时推出《从〈开卷〉现象说到民刊出路》,还有为《开卷闲话十编》所写的序言,正是他的出手不凡。休看只此两篇,若是从理论影响上着眼,借用南开大学教授陶慕宁评价《稗谈书影录》之言:“手此一编,晚清民国百年间之古代说部研究状况几可一览无余,其衣被于学人者岂浅鲜哉。”细品两文,它对《开卷》十五年发生发展的历程,几可一览无余。
为证实这几可一览无余,先看《从〈开卷〉现象说到民刊出路》中的分析:“《开卷》办刊伊始,就瞄准了高品位,实现了高起步。‘取法乎下’肯定不会有今天的《开卷》。旨趣的高低,取决于办刊者的眼光,也决定了办刊的水准,会直接影响她被知识界接受的程度。初期的《开卷》编委会,可谓是人才济济,这为她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并形成了朴素、优雅、轻松的个性风格(《纸香墨润》第一五五页)。”
此为《奇迹之一:高起步暨高品位的个性化办刊之路》;再看《奇迹之二:突破读书圈子和地域樊篱的影响力》:“《开卷》通过十五年的坚持,其实早以突破了‘读书’圈子的樊篱和江苏地域的阻限,形成了遍及全国的文化影响力。这一成绩来之不易,只有长时间坚持、高品质运行才有可能做到。影响力的形成,是需要发酵过程的,时间短了不行,水平低了更不行(同上第一五七页)。”
此外,还有《奇迹之三:从办刊到出版形成“产业链”》:“《开卷》不是为办刊而办刊,而是将其打造成強有力的整合文化资源的平台,进而介入出版和流通市场,形成文化产业链条。虽然真正算起经济账来,这种市场化的程度极其有限(个人酬劳恐怕更有限,很大程度上甚至无法抵消人力成本),但这种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将大批学人的阅读成果推向社会,其文化意义实在不容低估(同上,第一五七页)。”
《开卷》曾“创下单期印行一万册的纪录”,将它称之为“奇迹”并非过誉。据此,他认为:“《开卷》的发展之路占尽了天时、地利及人和。”而他能作出这令人信服的分析,从这段话中即可知其原由:
“我不知道‘《开卷》现象’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来的,但至迟二〇〇五年四月一日,《江南时报》记者倪方六在《民间文化刊物〈开卷〉受关注》一文中,就已经使用了这样的概念(同上,第一五六页)。”
由此可知,从它创办五年之时起,他就从理论角度来思考和分析《开卷》现象了。为了得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他除了仔细分析每一期的内容,还自二〇一三年开始,参加了在上海、株洲举行的两届民间读书年会。如果说这是为做调研而走出去的话,那么,在天津举办读书年会时关于民刊发展困境与突围的主题讨论,就是一次集思广议的检验结果。十年磨一剑,只为民刊事,如此的执着与勤奋,又怎不令人心生敬意?
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有关《开卷》发行学的问题,还未全面展开。他日成篇,一定像《开卷闲话十编》“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切入”一样,令人耳目一新。再看他就此所作出的三点概括,既会认同所言:
“一是记录读书人的选择。”“二是探究读书人的交游。”“三是解析读书人的心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闲话’堪称《开卷》的‘小事记’,乍看属于敝帚自珍之类,但随着刊物影响的扩大,再看这些文字就难能可贵了——它不只是一份读书民刊的成长历史,也是当代社会文化生态的忠实记录,因此无心插柳地具有了社会学上的意义。”
理论研究对于文本的意义,就是从所发生的现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再进行高度的概括。这样的文章并不多,只有他和陈辽等人的区区数篇,但仔细品悟它们,对《开卷》的理解,就如同“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会有别样的收获。而这样提纲挈领的文章,非有深厚的理论修养才敢着笔,有人称他是南开的高材生,并非浪得虚名。由此说来,《开卷》加盟于问津书院,真当额手称庆,他为此所付出的心智,也应书以成文、记录在册。
王先生正当盛年,问津书院又做得风生水起,《开卷》自然能从中大受补益。作为它的老读者,借此向他以示谢意,亦在还可饱其蠹腹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