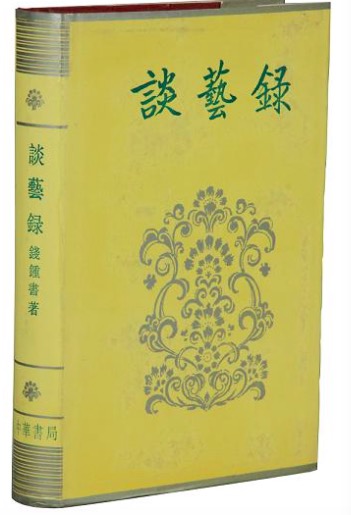***

玉蝉与玉蚕

玉蝉与玉蚕
钱钟书有段话颇发人深省。他说:“史学的难关不在将来而在过去,因为,说句离奇的话,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着的。……同一件过去的事实,因为现在的不同发生了两种意义”。又说,历史上的事实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史的事实,一类是史家的事实,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因为历史现象比不得自然现象,既不能复演,又不能隔离,要断定彼此间关系的性质,非常困难,往往同一个事实,两个史家给它以两种关系,而且都‘持之有故,言之有理’。我们为谨慎起见,只能唤作“史家的事实”。这就是所谓“过去的现在性”(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
由此看来,章学诚以“史”为中心来贯通“义理”、“文章”,就存在着种种困难。其一,史实难考;其二,史事性质难定;其三,丹青难写是精神。即便“志存良直,言有征信,而措词下笔,或轻或重之间,每事迹未讹.而隐几微动,已渗漏走作,弥近似而乱大真”。
怎么办?在不排斥以“史”贯通“义理”、“文章”的情况下,钱钟书便转换了立足点和视角,即分别以“文”和“理”为立场和视角来贯通“理”、“史”或“文”、“史”。
从“文”的角度看,他主张因文知世。他指出:“言不孤生,托境方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先圣后圣,作者述者,言外有人,人外有世。典章制度,可本以见一时之政事;六经义理,九流道术,征文考献,亦足窥一时之风气。道心之微,而历代人心之危者著焉。”
这里,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既然言外有人,人外有世,那么与其因世求文,不如因文知世。因为因世求文,容易造成强别因果的情况。比如“有明弘正之世,于文学则有李何之复古模拟,于力学则有阳明之师心自觉,二事根本抵牾,竟能齐驱不倍”。
而从因文知世看,在典章制度里,我们则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政治,在六经义理、百家道术乃至于一代文献里,我们则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风气。这样看来,不论道心如何微妙,历朝历代人心如何危险,都能向我们显现出来。
钱钟书《谈艺录》的重要取向之一,就是以文学为中心来贯通文史哲。如果说,因文知世还是对因世求文的一个反拨,那么,把握他的文学观才是弄懂他之所以能够打通文史哲的关键。
早在1932年,他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就指出刘勰《文心雕龙》有一个重要观点,即“综观一切载籍以为‘文’”。对此,他表示赞同并加以论证。第一,‘文者非一整个事物,乃事物之一方面。同一书也,史家则考其述作之真赝,哲人则辨其议论之是非,谈艺者则定其文章之美物;犹夫同一人也,社会科学取之为题材焉,自然科学亦取之为题材焉,由此观点之不同,非关事物之多歧。’
第二,对于文学语言来说,“言止于物,融合不分;言即是物,表即是里,舍言求物,物非故物。……删除其世眼之所谓言,而简择世眼之所谓物,物固可得,而文之所以为文,亦随言共去矣”。
第三“文学题材,随时随人而多损益;往往有公认为非文学之资料,无以取入文者,有才人出,具风炉日炭之手,化臭腐为神奇”。
第四,“文章要旨,不在题材为抒作者情,而在效用能感读者之情”。
第五,“文学史贵乎传信纪实,孔孟老庄,班书马史,此固历古词流,奉为文学鸿宝者……脱一笔抹杀,不与记载,则后世文学所受之影响,无可考见矣”。钱钟书从作者、语言、作品、题材、读者和文学史等角度,全方位地阐发了在常人看来壁垒森严、声气不通的文学与非文学之间仍然存在着众多交集。比如,观点创造事物;比如,言物关系;比如,宙合万汇百端莫非文料;比如,文学题材区域之扩张;等等,都可以作如是观。
这是一种开放的、以行文之美为核心的文学观。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载籍皆文”这一命题,并且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六经皆史”的一个鲜明对照。
从“理”的角度看,他主张以思想激活史料。他指出:“不读儒老名法之著,而徒据相斫之书,不能知七国;不穷元祐庆元之学,而徒据系年之录,不能知两宋。”在他看来,一部春秋战国史,不能仅仅凭借战争记录来了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以当时儒老名法百家争鸣的思想状态来把握其时代精神。
有宋一代,不能仅仅凭借着编年史来了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以宋代导学来把握其文化心理。正如他所说:龚定庵《汉朝儒生行》云,“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断章取义,可资佐证。
在《谈艺录》八四则中,他还指出:禅可以通之于诗。比如,严羽在学诗工夫之外,另捻出成诗后之境界,妙语而外,尚且有神韵。不仅以学诗之事比诸学禅之事,而且以诗成有神,言尽而味无穷之妙,比于禅理之超绝语言文字。
如果说因文知世是以文来贯通史、理,以思想激活史料、禅悟通于诗悟,是以理来贯通史、文,那么再加上以史贯通理、文,钱钟书就得以在着三个立足点和视角之间转换。这三个视角并行不悖,通而不同,各有优劣,互为补充。然而,钱钟书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继续寻求这三个视角的相通之处,进而提出“精神蜕迹”之说。
他说:“阳明仅知经之可以示法,实斋仅识经为政典,龚定庵《古史钩沉》仅道诸子之出于史,概不知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已。”在钱钟书看来,王阳明只是从政治角度讲经之效用,章学诚和龚定庵只是说经、子之来历,他们都忽视了经史子集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精神蜕迹”说则揭示出经史子集乃至于一代文献成为可能的条件在于:它们都是时代精神、文化心理的蜕迹和征存。精神或心理本身就蕴含着史、思、诗(文)这三个不同的维度。
因此,经、史、子、集乃至于一代文献不仅可以当“史”看,而且还可以当“思”看,当“诗”(文)看。比如,他既说“诗具史笔”,也讲“史蕴诗心“;既说“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也讲《论语》之“泠泠善语”,《孟子》之“汩汩雄辞”,《庄子》之“澜翻云谲,豪以气轹”,“其怡情悦性,视寻常秋士春人将归远望之作,方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既说“历史是一个大掌故”,也将“历史乃哲学以教人之实例”;
既说“头脑辩证法”别之于“情感辩证法”,也讲“情感之辩证,视观念之辩证更纯全正准,抒情诗作者具此相反相成之体会”;等等。
可见,“精神蜕迹”说是对“六经皆史”说的现代转换,它不仅为史学辟出了极为广阔的天地,而且展现出传统学术思想乃至人文学科研究的新视角、新观念和新方法。(《 “六经皆史说”与“精神蜕迹”说》;王达敏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1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