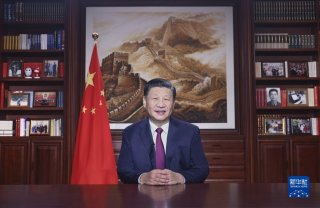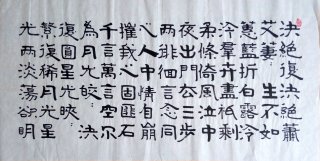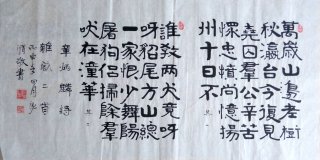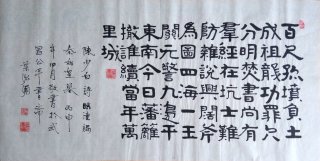这一时期的学堂从形式上看初具新式学堂的规模。学堂大多实行分年课程和班级授课制度,校舍不再沿用书院旧有房屋,而是鸠工庀材,改造书院集中于一处的讲堂为新式教学楼,并陆续兴建实验楼、自修室、操场等配套设施。由于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学堂课程也由原先单一的外文、翻译、算学等专门教育,发展为包括各种普通学科的完整的普通教育课程,添设了格致、历史、 地理、 音乐、 图画、体操等。 虽然办学仍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97页。] 读经讲经钟点过多,其他课程难免流于点缀。但毕竟有众多学校把以上科目列入办学章程,并努力付诸实施。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学堂的缺点仍很突出。首先,学堂官气太重。省城高等学堂、府中学堂一般由督抚委任观察为监督总理一切,县小学堂则多由教谕出任堂长或监督。学堂不能自行招生,一旦缺额多由官府出示招考,或直接札调书院高才生入学堂学习。学生考试合格后,仍须由地方官验看,合格后方能入学。其次,教习中新学人士不多。总教习不少仍由原书院山长担任,教习亦多聘请当地积学之士担任。教习中虽不乏饱读诗书学问渊博之人,但多因不懂教学方法而不能胜任教学。如苏州中学堂教习曹元弼,丝毫不懂新式学堂的教学法, “大率每月讲经五六次, 名曰经期,”每次“则曹率其弟子各乘轿而来,居中昂坐,闭目讲论其说”。[《苏州学堂记事》,《警钟日报》1904年7月23日。]仪董学堂总教习王鹏运“博学能文,惟于教育素未研究,故生徒多轻易之”。[《仪董教习猎角》,《警钟日报》1904年8月11日。] 有些教习甚至根本不上堂讲课,“以为每日在课堂安坐四点钟即为毕事”。[《武阳公学招考》,《警钟日报》1904年11月24日。] 或“惟看堂课(逢礼拜日学生作四书五经义史论之堂课,每期不过十余篇)”,[《投函高邮怨君》,《警钟日报》1904年4月27日。] 略加圈点而已。
(3)废科举后───学堂一枝独秀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科举制度,与科举制相关联的书院制度最终失去了存在的依托,随之宣告终结,新式学堂随之蓬勃发展起来。
苏中苏南各府一方面裁撤原先存留的各校士馆,把书院剩余的款向拨入学堂, 改善学堂办学条件;另一方面则把改办学堂推广到乡镇一级的小书院, 在这方面宜兴是个典型。 废科举后,东坡书院改为东坡高等小学堂,从此该院的校舍和经费都由学堂使用; 崇儒书院改为经正学堂; 临津书院改为临津高等小学堂;鹅山书院改为鹅山高等小学堂,滆南书院改为滆 南高等小学堂。[ 邵正芳《宜兴历代书院简介》,宜兴文史资料13。] 苏北徐淮海一带的书院则开始大批改办学堂。淮安府袁江、临川、崇实书院均于1906年停课,学堂在书院停后才陆续兴办。1906年即袁江书院改设清江县高等小学,二年后迁入崇实书院。次年临川书院与向善堂、延寿庵合并改设渔沟初高两等小学堂。泗阳淮滨书院1905年始改设青选学堂。徐州府登瀛书院1907年改为崇实小学堂,丰县精勤书院1906年始改为精勤小学。海州石室书院,1906年由知州张景祜开办海州中学堂,敦善书院次年开办北鹾中学。[ 据《江苏通志淮阴徵记册稿》、《民国泗阳县志》、《铜山县志》及各地文史资料。]
此后新式学堂不仅在数量上增长极快,在质量上也逐渐完善。突出表现在师资和生源两方面。前此由于新学人才缺乏,教习多不合格,不少新学课程也因而流行形式。1905年以后两江师范、宁属师范及苏省师范陆续有学生毕业,加之留洋回国学生日益增多,教习队伍因之有了很大改观,逐渐充实了师范毕业生或留洋学生。如高邮致用学堂。“日益腐败,现学界大动公愤,拟逐总办吴玉堂,另聘师范毕业生”。[《高邮学务两记》《申报》1905年10月15日。] 镇江府中学堂原“拟以赵辛银明经为监督,明经固辞,乃电承太守改李遵义为监督”[《中学监督易人》《申报》1906年2月4日。] 李遵义之友杨振声辅之,他“尝游东洋,详于规则”,学堂中凡“译音方伎,术有专门,课程簿支,月有分表”,[ 李遵义遗稿《南 学舍始末记》,镇江文史资料二十五第62页。] 皆由杨振声总其成。生源方面比前大为充足,彻底改变了学堂时常缺额屡屡招考的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大批生童从学堂发展的阻碍一变而为学堂的生力军。科举制废后,学堂招考屡屡爆满即很能说明问题。比如扬州仪董学堂学额仅设20名,以往仍常不足额。1906年的一次招考,“闻应考者约有一千余名,而学额仅设念名,遗弃未免太多”。[《申报》1905年11月1日。] 另一方面则由于学堂开始以培养普通国民为宗旨,人们已经认识到教育当注重普通,“普通云者,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217页.] 学生来源不在局限于举贡生童,而扩大到农工商各业子弟,凡有志于学者通过入学考试,交纳一定学费即可入学。
任何一项旧制度都不会心甘情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书院制度虽已终结,少数人仍蠢蠢欲动企图规复书院。苏府绅士为此不得不致书江苏学务总会,指出“书院者,为科举之预备也,无科举则无预备,无预备则无书院,彰彰明矣”。[《苏府紳士致江苏学务总会函》《申报》1906年2月11日。] 而存古学堂的设立,虽无书院之名而有书院之实。扬州校士馆停办后即开办尊古学堂,后苏省又拟照湖北存古学堂办法,就原苏州学古堂设立江苏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成就通儒”。[ 潘懋元《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敎育出版社1993年,第246页。] 存古学堂里面很有几位博学的教员,“曹叔彦元弼为经学主教,叶鞠裳昌炽为史学主教,邹永春福保为文学主教,三君者皆翰林也”,[ 商金林编《叶圣陶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2页。] 在保存古代文化方面有一定意义。然而当时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保存国粹,不足以补救大局,安全身家,况乎保存国粹之策,固别有在,无用此特殊之学堂,以淆乱教育之统序也”。[ 潘懋元《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敎育出版社1993年,第257页。] 因此一经开办,即遭到教育界人士的猛烈抨击。加之合格生源有限,财力匮乏,终于在辛亥前夕停办。而扬州的尊古学堂开办不久即改为两淮师范。可见书院制度存在的可能性已丧失殆尽,书院的最终消亡也仅止是个时间问题了。
2、新旧杂陈
纵观江苏书院改办学堂的历程,全省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进度上说苏南最快,苏中次之,苏北最慢。成效上看差异更大,不论是教师队伍、课程设置还是教学方式都呈现新旧不一错综复杂的局面,总体而言由北而南新学化程度越来越高。
(1)教师队伍
苏南及苏中地区学堂延聘外籍教师或新式学堂学生及有留学经历者较多。
1904年苏省师范学堂聘请“日本教习六员,中国教习五员”。[《师范学堂分聘敎习》《警钟日报》1904年11月27日。] 镇江府中学堂也于1905年礼延日本人八橘酿君为教习,“橘君于测绘理化科极有心得”。[《饬延日本敎习兼敎中学》《申报》1905年5月20日。] 在新式学堂开办之初,国内师资缺乏的情况下,借才异域不失为明智之举。此外聘请留洋学生为教习者也不在少数,如镇江府中学堂的杨振声,“尝游于东洋”。[ 李遵义遗稿《南学舍始末记》,镇江文史资料二十五第62页。] 吴县甫里小学开办人沈柏寒“曾东渡日本,就学于早稻田大学教育系”。[ 史承先等《吴县甪直中心小学简史》,吴县文史资料七第70页。] 武进前黄三近小学,数理教师徐晓卿,“秀才出身,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吴之光等《记教育界名人汤时斋》,武进文史资料十第53页。] 无锡东坡小学“担任日文的是溧阳姓王的老师,曾在日本简易师范读过一年”。[ 潘序伦《东坡书院史话》,宜兴文史资料一第66页。] 随着各地师范学堂陆续有学生毕业,苏南苏中各校又充实了大批师范生。如常熟石梅小学教员庞檗子,“江苏师范学堂肄业后在常昭公立高等小学西校任国文、历史等科教员”。[ 王化民《石梅小学史料琐集》,常熟文史21第149页。] 扬州府学堂“监督李少亭孝廉向肄业于苏州师范学堂”。[《镇郡中学堂大起风潮》《申报》1905年11月3日。] 靖江人陈卓如1905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后回靖,先后任靖江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师”,[ 陈公仰《我的父亲陈卓如》,靖江文史资料八第72页。] 靖江中学教师、教务主任、事务主任等职。宝应第一高等小学在1910年的时候,班级完全,教师大多是学校毕业出来的。[ 据《教育家朱白吾事略》,宝应文史资料七,文史资料委员会。]
苏北徐淮海一带教师队伍则明显不如南方。徐州府一些有识之士冲破封建教育的羁绊,为探索新的办学之路赴日留学或考察,时间已是1905年的留学高峰期。虽然他们学成回国后,对徐州新式教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与南方相比终究慢了一拍。而沛县“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李昭轩等人”[ 张基愚《沛县民国风云录》,沛县文史资料八第2页。] 民初始回国。宿迁张梓琴“乃愤而抛弃举业,与沈薪萍先生东渡日本,留学东京,进入宏文学院全科师范学习”。[《教育家张梓琴先生》,宿迁文史资料一,第100页,县政协文史研究会。] 学成回国,也已值民国初年。在这种情形之下,苏北各学堂教习大多由本地秀才举人担任,少数学堂毕业生并无用武之地。如乐育书院改建的丰县高小,“校长是同治年间的举人李运昌”。[ 陈益甫、杨化民《清未至1948年11月丰县教育发展概况》《丰县文史资料》四第120页。] 盱眙敬一学堂,“姚挹之,清末秀才,李尚亭前清廪膳生”[ 程希愚《校历四十 桃李逾千》,盱眙文史资料选辑三第12-13页。] 睢宁到民国成立后才开办学校,“本县仅有少数人在徐州师范学堂毕业回来,始终待聘,佟敏斋、张超吾、魏近礼等”。[ 张石南《辛亥革命后睢宁教育概况》,睢宁文史资料三第11页。] 直到1916年,沛县高小“有三年级的英语教师封介入,南京高等师范毕业,在沛县是当时仅有的”。[ 冯亦吾《民国初年我县的两次学潮》,沛县文史资料二第45页。] 这样的师资在当地仍称得上第一流。
(2)课程与教材
学堂开办之初课程较为单一,随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课程逐步完善,但具体执行情况仍有很大差别。苏南各学堂课程完备,且多使用新编教材,开风气之先。
首先,苏南各学堂均重视理化课程。长元吴三县高等小学堂开办不久,即派副办方令往上海,“将奉购理科、史科等各种教科书装运回苏”。[《图书购到》《警钟日报》1904年7月13日。] 常熟石梅小学算学科有附属科三,“甲曰格致、乙曰化理、丙曰绘图”。[《官学堂之现状》《警钟日报》1904年6月28日。] 镇江府中学堂初延“高君敬斋理化”,[《教习易人》《警钟日报》1904年11月11日。] 后又延日本教员八橘酿君担任,当时理化一科一直有“专门教员演习而手授”。[ 李遵义遗稿《南 学舍始末记》,镇江文史资料二十五第62页。] 苏州师范学堂为培养理化教习,增设的优级师范选科中,专设“物理化学数学”[《各省敎育汇志》《东方杂志》1906年第九期。] 一部。其次,均重视体操一科。1904年春,苏州各官办学堂除三县小学堂外均“奉文添聘体操兼课诸生”,秋后“苏府许守遵聘南洋公学毕业生林嘉驹到堂教授”[《警钟日报》《添设体操》1904年9月16日。] 体操,并有从上海购回的体操器械。昆山小学堂亦聘有体操教习教授体操。常熟石梅小学所拟章程设有体操一科,桂村小学,则在1906年添设体操,“以兵式为主,兼习瑞典哑铃”。[ 蔡瑞荣《由书院到学校》,常熟文史资料辑存十五第167页。] 此外,常熟石梅小学在推广国语方面亦属首创。1909年公立高等小学期间“为学生将来交接之便利而得语言统一之基础”,“增设国语科”。这项措施在当时是属开创性的,受到省视学的表彰,“有国语一科开创风气,可期语言统一之效,至可嘉尚”。[ 蔡瑞荣《由书院到学校》,常熟文史资料辑存十五第167页。] 次年,清政府才通饬各校添授官话。
与苏南相比,苏北乃至苏中均显落后。比如山阳县小学堂在苏南学堂已开设理化各科之时,“功课除通鉴辑览,古文观止、新闱墨三项外,惟间日课英文、算学”。[《山阳小学黑暗面》《警钟日报》1904年4月23日。] 高邮致用学堂虽开设体操及英文、算学,无奈总教习对之深恶痛绝,“学生请病假时则曰:此体操之过。”进餐时则“不肯与英文教习同桌而食,曰:非我族类”。[《投函高邮怨君》《警钟日报》1904年4月27日。] 发展前景可想而知。而扬州仪董学堂1906年前尚无专门体操教员,后来赵都转终于认识到“体操一科,有兵式柔软之别,学界最为注重”。[《申报》,1906年4月13日。] 才聘请曾肄业于巡警、陆师学堂,熟谙体操的俞诏春充当仪董中学体操教员。